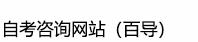央视主持人:4次高考才考上 被邻居调侃“大”学生
张泽群 1965年4月出生于河南郑州,1982年-1985年四次参加高考,终考入北京广播学院(现中国传媒大学)播音系。现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,2006年-2011年连续六次主持央视春节联欢晚会,2009年获金话筒播音主持作品奖。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
上世纪70年代末,恢复高考的头几年,在周围一片“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”的气氛中,张泽群在机关大院大礼堂里看电影,去学校排练文艺节目,做一个少年内心想做的事儿。
当高考降临在他身上,他看到的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:失败,就得去社会上晃悠;成功,则意味着拥有更多选择的可能。为了那一点儿“可能”,张泽群从1982年到1985年连续四次参加高考,终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。
他说,四次高考让他相信天道酬勤,相信公平正义,相信可以完全通过自己努力、不凭借任何运作,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
2013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,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张泽群坦言最关注教育公平问题,他还为河南考生呼吁“高考公平”。在他看来,天道酬勤、公平正义,是恢复高考之后在几代人心中确立的价值理念,在如今这个时代,更加不能变。
谈少年时光
“感谢父母没逼我去学习”
新京报:1977年恢复高考时,你对当时的情景有什么记忆?
张泽群:那一年我12岁,上中学的头一年。我生活在河南郑州的一个机关大院里,高考恢复的消息传到院里,立马就炸开了锅,那时候积累了很多“待业青年”,包括一些返城的知识青年,大都无所事事。听到消息后,他们都打算去参加高考。
有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,有一天院里来了一辆大卡车卖辅导资料,大伙儿都围着卡车买书。我爸也买了一套,是“文革”前出版的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,全是临时复印的,一共17册,捆成一扎。当时社会上已经流行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观念。我翻开一看,全都看不懂,我那时数学才刚学到因式分解。
新京报:你爸为什么也买了一套?
张泽群:主要还是一种氛围。当时在院子里,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高考。在高考中断期间,“大学”基本是淡出人们视野的词汇,但我不止一次听到过。1976年,我小学五年级,当地有个豫剧团演一场戏,把我拉过去当临时小演员,演完后,剧团想把我留下来当学员。那时候被剧团看上,相当于一下子解决了工作。周围人都说,孩子这么小就能出来挣工资了,多好的事儿。但我妈一口就回绝了,说“我们家孩子以后还要上大学呢”。一年之后,就恢复了高考。
新京报:所以你从小就生活在“要上大学”的氛围中?
张泽群:其实并不是,我爸妈只是模模糊糊给我指引了一个大方向,但基本上没怎么干涉过我,没给我下达过“一定要上某某大学”的指令,没让我承受过大的学习压力。中学开始,大院里礼堂每周放三次电影,一晚上放两部,我经常泡在里头。别人都在看书、学习时,我看了各种各样的老电影。高考恢复后,社会上已经开始有“不考大学没有出路”的观念,但爸妈从没逼我去学习,有时我爸还会主动去帮我拿电影票。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过得非常愉快,成了老电影的“骨灰粉”,为此我特别感谢我爸妈。
新京报:除了看电影,中小学时还有什么经历?
张泽群:我从小就喜欢文艺,是学校里的文艺积极分子。从我小学开始,学校里就有宣传队,很多孩子小学时还参加,上中学后就陆续退出了,但我还愿意参加。有天晚上我和我爸说在学校复习功课,其实是偷偷跑去排练节目了,我爸知道后也不骂我,只是说:“你要是喜欢排练就去,又不是干什么坏事儿,不用撒谎。”
初中时,有些孩子就立志要考大学,开始看更高年级的课本。我仍旧没觉得有什么压力,后来才慢慢感受到。
新京报: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这种压力?
张泽群:1981年高一要结束时。那时候高中只读两年,高二就要面临分班、高考了,我才发现自己的成绩真的落下了,已经跟不上其他同学。我开始准备复习,到了高二最后一个学期,我17岁,知道自己成绩不好,可能考不上大学了,才开始想:将来怎么办?
周围有一些没考上大学的年轻人,只能进入街道或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社,等待分配工作,说白了就是瞎晃悠。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儿,没有一份固定工作。等到我也可能面临这种状况时,才有点慌了。我就是不想在社会上瞎晃悠。
2017年暨南大学自考全日制免试入学报读咨询电话或微信号13316198699
2017年暨南大学自考全日制免试入学报读咨询电话或微信号13316198699